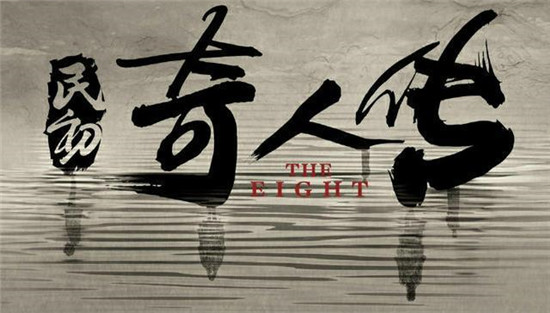你可能看著《薰衣草》、《王子變青蛙》走過花季雨季,也可能為《杉杉來了》的“魚塘夫婦”突然流行不明所以,又或者驚訝于《何以笙簫默》引領的“霸道總裁”流。但是,如果你以劉俊杰導演這些過往作品,去推論他正在拍攝的電視劇《涼生,我們可不可以不憂傷》,那么,最后你一定會大吃一驚。
已經(jīng)被湖南衛(wèi)視鎖定首播權的《涼生,我們可不可以不憂傷》,跟大家所料想的可能都不一樣。
這部電視劇完全不同于當下市場的言情劇,也突破了導演以往的風格,甚至比起原著都添了一抹溫暖。而且,不只是作品層面、創(chuàng)作理念的不同,從整個劇組的工作方式到演員表演、拍攝手法都迥異非常。《涼生,我們可不可以不憂傷》已經(jīng)變成了一個所有工作人員用自己的匠心和審美詩意,以手工的方式,反復打磨每一個細節(jié)的手工作品。
導演劉俊杰說,有匠心的手工品才是獨一無二,才最值得珍藏。

回到初衷而又追求粒粒包金的“手工品”
兩年前,制片方(慈文蜜淘影業(yè))帶著5本小說找到劉俊杰導演。他只看了《涼生,我們可不可以不憂傷》第一部前半部分,就決定要拍它。之后,他沒有接任何戲,也沒有接任何工作,半年時間都用這部戲的準備上。
據(jù)說,不只是參與劇本,這部戲的每個演員導演都自己去挑,每個景他都自己去看,每一場戲他都自己拍自己剪,每個聲音和音樂他都自己放進去。
當導演坐到我面前時,說起自己經(jīng)常收工回家,徹夜難眠,情緒亢奮,我一點都不驚訝。第一眼就可以看到:他的心思,他的生活,他的整個人,都已經(jīng)陷進了《涼生,我們可不可以不憂傷》這部電視劇當中。交談中,你跟他談演員,他很快會繞回角色。你跟他談市場流行,他一定會回到自己的創(chuàng)作理念。
在開機儀式上,劉俊杰把自己千言萬語,最后匯成了四個字:莫忘初衷。
那么,拍這部劇的初衷是什么?
劉俊杰覺得是要回到人的情感,回到人性人情人的內心。他早年拍戲,喜歡用大量柔焦,追求漂亮唯美。但他發(fā)現(xiàn),不管拍給年輕人的青春劇,還是拍給女性的言情劇,或者拍給白領的都市劇,婆婆媽媽看的生活劇,還有古裝劇,不管那種類型,最后都繞不開人的情感。所以,這一次他想不再刻意追求強情節(jié),也不要花架子的華麗場景,用最簡單的方式打動觀眾的內心。

他認為故事不只要情節(jié),更要情感;演員要心態(tài),不要姿態(tài);表演要神似,不要形似。
劉俊杰舉了一個“蛋炒飯”的例子。很早以前,他吃過一種蛋炒飯。老板很自豪,說自己的蛋炒飯“粒粒包金”,如果吃到一粒米飯沒有被蛋包著,那就退錢。材料是最簡單的:蛋、米飯、蔥,但其實技術上一點也不簡單。那么,“蛋炒飯”也是他對這部劇的定位:既沒有觀看門檻,所有觀眾都吃得起;還要又干凈又好吃,讓大家喜歡吃;最后還是主食,餐餐吃不膩。
同時,這部劇也要“粒粒包金”,也就是細節(jié)上做到完美和真實。例如某個情節(jié)發(fā)生在上海的大戶人家,飯菜就得符合上海大戶人家的特點,吃什么,怎么吃,細節(jié)上有講究。同時,飯菜必須現(xiàn)做,演員把筷子拿起來,就可以熱氣騰騰地吃飯,攝像機再捕捉下來,才會有特別真實的感覺。實際上,這個大戶人家的阿姨、管家,劉俊杰都在上海專門找了個老師傅訂做衣服,設計發(fā)型。
那么,作為導演的初衷呢?劉俊杰很喜歡“匠心”這個詞。
他認為一個導演,前面的劇本沒有參加,演員別人挑的;到現(xiàn)場按套路拍完;后面的事又都交給剪輯師,這是不負責的,最多只做了三分之一的工作。當然,從零開始,前期設計、中期拍攝、后制都參與進去,也是應該完成的工作而已,還不算事業(yè)。
劉俊杰覺得拍戲就該像是一個手工匠,用自己的匠心打磨每一個人物、每一個場景、每一個道具、每一個鏡頭、每一首曲子、每一次情感。把所有文字變成劇本,把所有人物立體化到一個個演員,把所有場景都還原出來,最后再用影像呈現(xiàn)出故事和情感。這樣才是一部完整的有美學風格的作品。
就像他現(xiàn)在于《涼生,我們可不可以不憂傷》這部劇中所做的事,他正享受這種把一部戲一點一滴打磨成手工精品的感覺。
要情節(jié)更要情感,有力量還要內斂,就像散文式小說
劇中有一場戲。未央婚禮,涼生前一晚走了。在婚禮現(xiàn)場,白色的玫瑰花,白色的桌巾,紅色的燈籠,新娘穿著紅色的衣服,大大的禮堂只有白色和紅色。未央就一個人坐在那里,陪伴新娘的只有站著的服務員,新郎沒有來。鏡頭就這樣對著她,半身的景,沒有對白,然后機器開始往后拉,兩分半鐘。
這就是劉俊杰喜歡的呈現(xiàn)方式:一個鏡頭,未央內心的世界全部展露無遺。
因為《涼生,我們可不可以不憂傷》本身的故事已經(jīng)足夠強情節(jié),所以,劉俊杰在尋找自己的拿捏尺度。如果照著拍,可能會有些狗血。而且,一場接一場的強情節(jié),觀眾看得會很累。若是缺乏情感作為支撐,觀眾不但不被打動,還會覺得不是拍劇的人弱智就是把自己當弱智。
劉俊杰的拿捏尺度,就是把《涼生,我們可不可以不憂傷》拍成一篇散文化的小說。不是不要“強情節(jié)”,而是要還強調“情感”。就像村上春樹的小說,很自由自在地寫,但真情實感一直在,一下子就能打動讀者的心。
因此,劉俊杰總是提醒演員:你很傷心,但我不見得要你哭。你很開心,你不想笑就不笑。重要的不是表象,而是呈現(xiàn)出角色真實的情感。最難過的時候,淚光只在眼眶里閃爍,也許比流出來更打動人。重要的是進入了角色,而不是拘泥一些形式。相反,演員只會拿著劇本念念念,沒有情感,沒有情緒,那才是最可怕的。
就像孫怡進組的第一場戲,之所以打動他,就是一句對白都沒有,卻把姜生心結已解的情感很細膩地呈現(xiàn)了。
那是回到“魏家坪”老家,姜生小時候對父親很仇恨(父親背叛母親),但是,父母現(xiàn)在都已經(jīng)走了。那么,該如何呈現(xiàn)這種復雜的情緒呢?一般電視劇都是哭天喊地。而他們沒有一句臺詞,孫怡只是靜靜地看著父母的遺照,沒有掉一滴眼淚。然后,走進院子,把父親生前有些脫落的舊輪椅,用線重新纏繞起來,再把輪椅放好,好像父親還會再坐一樣。這時,她的眼淚才掉下來。
干凈的畫面,簡單的音樂,內斂至安靜的力量,有情感支撐的情節(jié),這才是劉俊杰想要的。
要心態(tài)不要姿態(tài),演員和角色渾然天成
《涼生,我們可不可以不憂傷》每個角色都很難演,沒有大量的對白,又都有太多的故事了。因此,劉俊杰覺得既然難演,那干脆不要演,畢竟怎么演都會落了痕跡。一般的電視劇選擇演員,是你會演戲,所以我請你演這個角色。那么,他反過來了,是因為你的內心能找到這個角色,所以我用你。這樣的話,演員就不用演了,你就是角色,角色就是你,關鍵是從演員的內心能找到這個角色的“魂”,能渾然天成。
古龍說劍法到了化境,是“人劍合一”。他的思路正是“人戲合一”。
鐘漢良則是跟劉俊杰第二次合作,之前在《何以笙簫默》兩人已經(jīng)合作過。“程天佑”這個角色,跟鐘漢良以往的角色不太一樣。他以前的角色大多溫文儒雅,而程天佑這個角色很癡情,對姜生的愛無止盡,可翻起臉來又很可怕。就像一面是天使,一面是魔鬼,沒有中間地帶,要么0度,要么100度。
劉俊杰再次見到鐘漢良,第一眼就感覺到整個人完全不一樣。跟上次合作相比,此時更成熟,對角色的拿捏更精準,就像一個美國牛仔變成了英國紳士。這種演員的成長感很清楚,正好符合程天佑的內心層次感,立刻就覺得程天佑非鐘漢良莫屬。
之所以選擇馬天宇來演涼生,也因為如此。劉俊杰和馬天宇在北京見過一次面。通常,導演和演員見面,都會聊故事、聊角色,但他們沒有,反而聊孤獨、聊流浪、聊人生、聊音樂。劉俊杰從他的內心看到了孤獨,看到了涼生的氣質。聊完之后,他就覺得這必須是涼生,不會再有另外一個人選。
當然,不是永遠都能找到那么完美符合角色的演員,那么,他會追求“神似”。就像“小九”這個角色,小說當中是個很外放的女孩,頭發(fā)染了七八種顏色,一出場是個“小太妹”。但并不好找,劉俊杰最后倒過來找演員,選擇了一個比較文藝青年的女孩李夢,她身上有股淡淡的憂傷。但是,骨子里有一種搖滾精神,所以成為了一個驚喜。
為了讓演員有最大的發(fā)揮空間,劉俊杰還改變了整個劇組的工作方式和理念。通常拍戲,都是演員配合機器,在一個范圍內表演。劉俊杰不再按套路去拍,他先把整個場景設計好,把所有細節(jié)都做到位。例如搭景,可能以往只需搭三個面就可以,但他會要求完完整整地把一個房子放進棚里,不能有任何穿幫的東西。然后,他請演員從頭到尾排一次,也不是跟副導演等對詞,而是和對手。
最后,演員再從頭到尾一次演完。依然跟其他人拍電視劇不同,演員不用配合機器,而是攝像師用4臺攝像機主動去捕捉演員的呈現(xiàn)。劉俊杰甚至要求鏡頭要能隨著場內的呼吸而律動,這樣畫面看起來可以很連貫流暢,而不是遠景近景那樣碎片化切來切去。
當然,不一樣的方式和思維,會帶來不一樣的新鮮。只是這也同樣意味著對整個劇組所有工作人員有不一樣的要求。得益于整個劇組超過八成的工作人員,都跟他合作過多年,所以費盡周折,還是找到了改變。
擔心以后不會再有機會能拍這樣的一部戲
劉俊杰不抽煙,不喝酒,也沒有任何應酬,每天就是工作,然后回家。自這部電視劇開拍,已經(jīng)完全“吞噬”了他的所有心思和時間。而他也找到了自己的“詩意”去構建這一故事世界,呈現(xiàn)所有人物的情感。
他在片場,隨身還一直帶著一本筆記。那是他看完書后,對所有故事和人物關系的梳理。一共有三十多個章節(jié)部分,然后每部分都用簡單文字進行概括:例如“你是涼生,千真萬確”;再如“血戒為盟,一生之痕”;還有“千島湖心,你在我心”、“三十而立,背城而去”……,都非常詩意。
這個注解上對于“十年涼生,此情天佑”的結局,也很詩意地寫著“此生相遇,便是團圓”。
當下的電視劇大多追求強情節(jié)、快節(jié)奏、華麗的包裝、夸張的表演。這一場打人耳光,下一場下跪,再下一場痛哭流涕。在這其中,《涼生,我們可不可以不憂傷》就是一股不一樣的“清流”。
劉俊杰坦承,自己并不想打安全牌,在套路里生存:“不想靠那些外力,那些夸張聳動的情節(jié)來吸引人,我想用內在的情感來吸引觀眾。因為現(xiàn)在所有的情節(jié)、套路、橋段,觀眾都基本上看過了。”
所以,很多人稱他為“臺灣偶像劇教父”,他其實不太喜歡。
但是,拍完這一部戲以后,是否還會有這樣的機會,再拍一部自己所有的審美詩意都可以被實現(xiàn)的戲。劉俊杰也不知道,他也擔心,他只能說:《涼生,我們可不可以不憂傷》是獨一無二、不可復制的,包括對于他自己來說。
對話錄
《涼生,我們可不可以不憂傷》是一部強調回到初衷的戲
記者:您似乎多年如一日在拍“偶像劇”,聽說這次不一樣?
劉俊杰:最近這一兩年來,我覺得自己也改變了很多。我拍了這么久的快40年的戲,不管是所謂的偶像劇還是其他類型的劇,古裝、時裝還是現(xiàn)代的題材,也不管各種各樣的情節(jié),我都已經(jīng)拍過。但現(xiàn)在尤其是此刻,我個人最想表達的還是最基本的一點:人的情感。我覺得不管什么內容作品,最后要抵達的其實還是人的內心。
大家都會說,導演,你以前似乎總拍偶像劇,但我也不太會覺得這是偶像劇。如果我把它定義在偶像劇的范圍之內,那可能就會只有年輕人喜歡,婆婆媽媽們不喜歡。但實際上,我想說的是,我拍的戲,我所有的想法,其實都想跟所有年齡層的人分享。生活中每個人都會有情感,不是只有年輕人才有情感。只是此時此刻與當時,我的理解和心境有所不同而已。
記者:就是“我手拍我心”。我也覺得真正的言情劇不排斥年齡大的人。就像一個白發(fā)老人看著老伴,經(jīng)歷無數(shù)生活的顛簸,眼里還能找到少年初見時愛情的單純,那不知多美好。
劉俊杰:所以我說要回到人的情感,你拍進去了大家都會想看。我很多工作人員都跟我一起工作很久,攝影師跟我合作了20多年,剪輯師有10多年。他們就說,你這一兩年拍戲有些變化,以前你喜歡拍的很華麗、很漂亮,所有情節(jié)都很夢幻,但這幾年卻往真實的方向靠,更注重人的情感。
當然,它還是需要藝術的包裝、戲劇的手段。不是說真實,就是把每天起床、洗臉、刷牙、漱口、出門,這些一地雞毛的瑣碎都再現(xiàn)出來,那沒有什么好看。既要真情實感,還要用最合適的戲劇手段。
記者:藝術真實不等于生活真實,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。我能理解,您擔心形式過于內容。
劉俊杰:單純的華麗的場景,我已經(jīng)不再在意,更注重的是戲劇本身所承載的情感和主題。當然,不在意不代表說隨便找個場景就可以拍,只是說不為了華麗而華麗,如果會華麗一定是因為應該華麗,需要華麗,可以為整部戲加分。就像在《涼生,我們可不可以不憂傷》開機的那天,大家都要講話,我不可免俗。我就說了四個字:莫忘初衷。
我拍戲最初的想法,就是把一些美好的故事和情感呈現(xiàn)給大家。我覺得沒有必要去刻意弄些花架子的形式,然后忘了故事的本真,忘了人性人情。就好像我們去餐廳吃飯,山珍海味,菜式精美,裝修漂亮,甚至連餐盤都很名貴,但是,菜不好吃。那么,你有可能會不如在一個小攤子吃得飽,只要小攤子的東西味道不錯。而我現(xiàn)在想做的,就是讓這些菜既干凈衛(wèi)生,看起來舒服,還吃起來很好吃。
《涼生,我們可不可以不憂傷》是一盤“粒粒包金”、有職人匠心的蛋炒飯
記者:可以舉例來形容您的初衷嗎?
劉俊杰:我覺得我現(xiàn)在拍戲的初衷,就像在做一個蛋炒飯。很早以前,我曾吃過一種蛋炒飯。那個老板很自豪,他說,我的蛋炒飯“粒粒包金”,如果你吃到一粒米飯沒有被蛋包著,我退錢給你。哇,這個蛋炒飯看上去簡單,其實技術上上一點也不簡單。我現(xiàn)在拍戲要的就是這樣的感覺。
那是最簡單的食物:蛋、米飯、蔥,然后就沒有了。我要做的就是:既沒有消費門檻,讓所有觀眾都吃得起;還要既干凈又好吃,讓大家都喜歡吃;最后它依舊是主食,你可以餐餐吃,吃不膩。如果所有戲都追求強情節(jié),快節(jié)奏,華麗的包裝,夸張的表演。這一場打人耳光,下一場下跪,再下一場痛哭流涕,我覺得其實并不打動人。最打動人的,往往是簡單平淡而又不簡單的情感,一種安靜而內斂的力量。
記者:簡單而又不簡單,或者說深入淺出,也就是“粒粒包金”的蛋炒飯?
劉俊杰:我拍了這么久的戲,差不多所有的套路都拍過了。拍給青少年看的青春劇,拍給女性看的言情劇,拍給白領看的都市劇,拍給婆婆媽媽看的生活劇,還有古裝的劇,但不管那種類型,最后都繞不開人的情感。這一次我想做不一樣的嘗試。《涼生,我們可不可以不憂傷》這部戲跨度很大,類型元素很多,青春的、偶像的元素都有,要定位觀眾很容易,但我不要觀眾門檻,我要尋找共性。但在創(chuàng)作上,我每一個細節(jié)都力圖做到最好,“粒粒包金”。
像小說里的“魏家坪”,那是涼生、姜生童年生活的鄉(xiāng)下,但又不屬于21世紀。今天的觀眾熟悉但又不容易看得到。那個地方我找了很久,最后找到浙江開化,從上海開車過去要6個多小時。到了開化之后,還要開1個多小時的車,才能到山上。這是一個保存得非常完整、很古老的村莊,看不到任何現(xiàn)代(21世紀)的東西。
這種過程很累很奔波,我可以找個景應付過去,但這就是一個拍戲的人應該持有的態(tài)度:不是說把以前的成功方程式——那部戲的套路觀眾喜歡看,然后復制過來照著拍。也不能說“用生命拍戲”,用生命太重了,但起碼可以做到很“用心”。自己的名字既然打在片頭片尾,就要負這個責。
記者:聽說投資方帶了幾個項目給您,您一眼就相中了《涼生,我們可不可以不憂傷》,然后一年都投入了進去,參與劇本打磨,你自己看景,自己談演員?
劉俊杰:嚴格來說,準備有兩年。兩年前,苗總(慈文蜜淘影業(yè)總經(jīng)理)拿了5本小說給我。其中,我只看了《涼生,我們可不可以不憂傷》第一部前半部分,就已經(jīng)被里面的情感所打動,我說要拍的就是它了。然后,我把小說讀完,再重新解讀了一遍。過年以后,我沒有再接任何戲,也完全沒有接任何的工作。因為我想讓自己靜下心來,專心把《涼生,我們可不可以不憂傷》拍好。
我設定的開機時間是在九月十月,因為我覺得這個故事特別適合秋天和冬天。規(guī)劃好后,我開始看場景和挑演員。每一個場景都是我自己看的,每一個演員都是我自己挑的,可以說,這部戲完完全全呈現(xiàn)了我自己想要做的東西。當然,也要感謝投資方給了我很大的空間,全力支持我。我大概花了半年的時間,去北京選演員,去法國看景,去浙江開化找到了“魏家坪”。
我說莫忘初衷,拍戲本就應該是這樣的。不是我把前面的戲拍完,接著進組又照著劇本拍,拍完又去下一部戲。不是這樣的。我是從“0”開始,把所有文字變成劇本,把所有人物立體化,并具化到一個個演員,把所有故事和場景都用影像呈現(xiàn)出來。我覺得這是很難得的經(jīng)歷,讓自己靜下來,慢下來,每一步腳印,都親自踩過。當然,還有很多工作人員這一年也幾乎只做這一部戲,跟我一起投入進來。
記者:這有點像在手工做一個藝術品。
劉俊杰:也不敢說是藝術品,但確實就是一個有匠心的手工品。拍戲本就是要有匠心的事,不可能標準化去生產,不是拿了劇本趕快照著拍完,然后趕場進組再拍。一年多拍幾部戲,可以多賺一些錢,但這樣不好。不要被太多的商業(yè)沖淡了初衷,還是要留下一些什么,對你的觀眾負一些責。
由于投資方全力支持我放手去做,這也是很難得的經(jīng)歷。通常拍戲嘛,投資方會有想法,我們大概拍個什么樣的戲,會有多少預算,用什么樣的演員。你就會有一定的限制,包括會給你幾個演員。像這部戲非常特別,從頭開始都以我的想法為主,一步步往前走。這就是一個導演最幸福的事情,所有的事情都能按自己的創(chuàng)作想法去做,每個演員、每個場景、每個道具甚至包括每個工作人員都是我自己挑的。
《涼生,我們可不可以不憂傷》是一個手工品,手工品往往獨一無二
記者:就算投資方等客觀條件許可了,有的導演、演員等主創(chuàng)也并不想花那么多心血,只想著能做一個及格的產品即可。
劉俊杰:拍戲是一個手工藝人的活,我一直說“職人匠心”,就是當你做這件事了,就什么都不要管,以盡力去做好這件事排在第一位。我有次去日本,看見一個拉面館上面寫著:“一生學面”。用大白話說,就是這一生只做一件事:做面。
這帶給我很大的感觸。因為我從20歲到現(xiàn)在60歲,這一輩子也沒有做過別的,就只會拍戲。要分清楚工作和事業(yè)的區(qū)別,工作是你付錢我做事,事業(yè)是你內心要先想做這件事,甚至是一輩子想要做的事,不是付錢去驅動的。所以我去拍戲,從不會跟投資方談我工作多久,你給我多少錢;而是我們想拍什么,我們有什么共識,我們能做出什么來。不是利當先,而是事在前。利在前最后往往什么都沒有,而事在前,事成其實可以利自來。
記者:兩種境界就像吃東西,一種是我餓了去吃,一種是因為它是美食我去吃。后者當然最理想,既解決了肚子,還有口舌的享受。
劉俊杰:所以我拍戲,一年最多只拍2部戲。人也需要休息,中間我會去旅行,把自己放空,吸收新的東西,然后再帶著全新的思考和狀態(tài)回來。而不是一部接著一部,你狀態(tài)不好,你疲于奔命,你機械性地重復,你就很難拍出好的作品,也是不負責任的做法。
做我們這一行的,開始都會想把每一部戲拍好,但到后來,有的受限各種條件,有的因為利益,前面的劇本沒有參加,演員別人挑的;到現(xiàn)場按套路拍完,拍完就走;后面的事都交給剪輯師,拍更多的戲賺更多的錢。那確實一年可以多拍好幾部戲,然后所有的戲都大同小異,觀眾可以猜到劇情,可以猜到什么時候切鏡頭。
我覺得作為導演,自己首先不應該有這樣的心態(tài),所以我跟所有人說莫忘初衷。不管最后有沒有成功,但至少你自己努力了,盡力去做好這一部戲,把作品留下來,讓更多觀眾記得。
記者:導演不是標準化生產中的技術工人。
劉俊杰:如果只做技術工,就是套路化嘛,是可以很容易把一部戲拍完。但這樣不享受,只是每天在拍而已。還有的導演都布置給執(zhí)行導演去拍,自己每天在劇組里開“鬼房”,這樣不行。我真的很享受一部戲一點一滴打磨出來的感覺,我的戲每個鏡頭都是我自己拍的,就像一個工匠用匠心在做一個手工品。
記者:手工品往往獨一無二,還是奢侈品。
劉俊杰:《涼生,我們可不可以不憂傷》的時間跨度很大,從1997年一直講到2016年。從姜生的敘述視角來說,要呈現(xiàn)幼年、初中、大學以及現(xiàn)代四大部分。我是按照這個時間順序去拍,也等于是伴隨著這些角色去成長。演員分三批,一部分是幼年的,一部分是中學時代的,到大學時代就是主演飾演了,但依然要經(jīng)歷從校園走向整個社會。我的感觸也很深,因為等于是看著這些角色長大,就像看著自己家的小孩一樣。
有些事要還原當時的場景,雖然只是過去十幾年,但如果要呈現(xiàn)細節(jié),其實難度很大。例如再去看1997年,大家都熟悉,可其實中國的變化又如此大,反倒時間跨度更久遠更容易處理,所以這次開機之前,我花了整整半年去看每一個景,去跟每一個演員見面。音樂也是我自己談的,跟林海老師聊了幾天幾夜,分享劇里的情感,然后他再做音樂。拍一部戲不只是把故事理解完,再把畫面拍完,而應該是一件很需要匠心的手工活,甚至說是去親手帶大一個孩子也不為過:細到每一個場景、每一個道具、每一個鏡頭、每一首曲子、每一次情感的呈現(xiàn),都需要去打磨。
拍的時候,你會很開心,也會很痛苦,更不會覺得累,因為你已經(jīng)沉浸在由角色所構成的世界里面。就像西方人常說的,每一個手工品都是不可以復制的,這樣出來的作品看起來一定會有些不一樣。是好是壞,觀眾是否喜歡,我不知道,當然,我希望觀眾喜歡。但是,它真的跟其他電視劇不太一樣,包括我在拍攝的時候整個思維都改變了,從根本上有改變,然后包括每個鏡頭都跟一般的電視劇不同,我自己都覺得很獨特。
《涼生,我們可不可以不憂傷》這部劇很不一樣,獨一無二。就算下次我再來拍這部戲,也拍不出這樣的感覺。包括過去我拍的每一部戲,都有我當時最真實的情感和心境,無法再復制。我個人喜歡把自己正拍的戲當最后一部戲,拍完就不拍了,拍不動了,退休了。
靠所有人改變,《涼生,我們可不可以不憂傷》才能從手工品變藝術品
記者:您的理念,具體在拍攝上是怎么執(zhí)行呢?
劉俊杰:我們不是常規(guī)的套路拍法,會先把整個場景設計好,讓演員從頭到尾演完,然后用4臺攝像機去捕捉演員的呈現(xiàn),鏡頭要隨著場內的呼吸而律動。這樣畫面看起來會很連貫、很流暢,而不是遠景、近景那樣切來切去,那樣就碎片化了。這對演員、攝影、燈光、道具等劇組每一個人都是挑戰(zhàn),需要他們先有思維的改變。
例如搭景,可能以往只需要搭三個面就可以了,但我這樣的拍法,就意味著搭一個房子,得扎扎實實、完完整整地把一個房子放進一個棚里,360度包括從屋內看到屋外、從屋外看到屋內,都不能有任何穿幫的東西,必須很真實地呈現(xiàn)。
再像我對道具組的要求,這個場景發(fā)生在上海的大戶人家,飯菜就得符合上海大戶人家的特點。肯定不是去餐廳隨便點幾個菜就可以,吃什么,怎么吃,細節(jié)上都有講究。同時,飯菜必須現(xiàn)做,演員把筷子拿起來,就真的可以熱氣騰騰地吃飯,然后攝像機再捕捉記錄下來。這會很真實,演員也容易入戲,不是說擺上道具菜,一拍完演員就立刻吐出來。
我想把這些拍戲的套路全部改變,每一個細節(jié)只要我能想到的,都會想盡辦法做到。就像程家是一個富豪大家,里面會有不少阿姨、管家,按理這些角色的衣服只要樣式差不多就行了。但我不是,我在上海專門找了一個老師傅訂做,也包括她們的發(fā)型都專門設計。雖然難免會有疏忽,但必須盡力把每一個細節(jié)都做到完美,包括每個角色應該穿什么樣的衣服,住在哪里,用什么樣的東西,去什么樣的餐館,都要思考。
記者:這樣工作量極大?
劉俊杰:當然,其實并不省時間,必須整個劇組的人都有思維的改變,才能做好。整個劇組85%的工作人員,都跟我合作過多年,都知道我的拍戲方式,但也依然需要先有思路上的改變,我自己也大概用了兩個月時間才找到這種方式,也摸索了很久。不是把燈光做好,把道具做好,就能改變,必須全組的人都到位了,才可能節(jié)省時間。就像我不會對攝影師去說,你要拍近景你要拍遠景。我把戲排完,大家專心聽。你聽懂了,有了戲感,自然會拍好。不然,你會根本不知道要做什么。
有想法是很棒的事情。不然,導演說做什么,然后大家只會做什么,那就只是個工具。包括演員也是一樣,如果只會拿著臺詞念念念,沒有想法,沒有情感,這句話應該怎么說,這個情緒應該如何呈現(xiàn),都不知道,那樣肯定不行。
記者:這樣觀眾和演員都很容易入戲?
劉俊杰:對。當我們把這些細節(jié)都做得很真實、很到位,演員演起來就會很自在。有時,演員進一個房間會說,怎么看不到一個燈?我當然不是不打燈,而是早已經(jīng)設置好了,讓它不妨礙演員的發(fā)揮。也不會一坐下來就告訴你,別動,米菠蘿在那里,你會出話的。這樣,演員一進入這個景,會很自在,因為他不受限制。這是你在劇中的房間,你進來就會感覺到,這就是你的房間。
這需要很多的磨合,每一組的磨合,例如四臺機器360度在拍,不能互相打架。所以我說要有徹頭徹尾的改變,要把以前那些套路化的思維全改變掉。可是,我覺得拍戲本該是這種狀態(tài),這里有花,就是真花。這里有水,就是可以拿起來喝的。這里有個廚房,就會可以做菜。這樣拍起來會很不一樣,沒有演的痕跡,很真實很真實。觀眾入戲了,就很難跳脫出來。
記者:創(chuàng)作理念會折射創(chuàng)作者的心境,您似乎內心狀態(tài)很單純。當然,已經(jīng)歷過歲月的沉淀。
劉俊杰:我是一個生活比較簡單的人。我比較喜歡狗,然后在臺灣的時候,我就會去收養(yǎng)很多的流浪狗。我的世界也很簡單,沒有其他的雜念,每天就是好好工作。工作就是拍戲,然后回家,我住在上海嘛。也沒有任何應酬。我不抽煙,也不喝酒,吃的東西也不多。因為中午吃的多,下午就會容易犯困,所以我中午吃的很少,主要是晚上回家吃。長期保持這種習慣后,工作時我一直能保持很好的精神狀態(tài)和身體狀態(tài)。
我很喜歡聽音樂,因此我覺得影像拍完之后,好的聲音非常重要。影像和音樂一定要結合起來才能打動人。像這次《涼生,我們可不可以不憂傷》,音樂我找的是林海老師。他的音樂很簡單,就是一架鋼琴,什么都沒有。但是,最簡單、最純粹的聲音,往往最容易打動人。干凈的畫面,簡單的音樂,這樣放在一起,就像是一篇散文。
當然,情緒會自然延伸,我也不會把情節(jié)拿掉。只是一場接一場的強情節(jié),觀眾看得會很累。一場強情節(jié)“爆發(fā)”之后,觀眾就需要舒緩一下,那么,干凈的畫面,簡單的音樂,就會恰當好處。因此,這次《涼生,我們可不可以不憂傷》有點像是散文化的小 說。他不會說“散”到你看不懂,“散”到很零散沒有情節(jié)。只是說很像村上春樹的小說,很自由自在地寫,但情感一直在,一下子就能打動你的心。
《涼生,我們可不可以不憂傷》是散文化小說,要情節(jié)更要情感
記者:這部戲您很強調真情實感,以及簡單呈現(xiàn)?
劉俊杰:我希望這部戲用最簡單的方式來呈現(xiàn)感情,因為《涼生,我們可不可以不憂傷》的故事已經(jīng)太強情節(jié)了。如果照著拍,就可能會狗血,所以怎么拿捏它?我自己有個比喻,就像一個深水炸彈,如果收一收,不讓它炸出海面。或許沒有沖天的水柱,但整個海面會更波濤洶涌。
我拿捏的尺度,就是把《涼生,我們可不可以不憂傷》拍得像一篇小說化的散文,或者散文化的小說。每個畫面看起來都有美的感受。這其實就是一線之隔,很容易走偏,如果我自己一放,就會只剩下強情節(jié)。所以選演員的時候,我說姿態(tài)不重要,心態(tài)很重要,你把心態(tài)給我。就像情節(jié)重要,但情感更重要。
光這些思路,就跟市場上一般的電視劇不同。大部分電視劇嘛,這個跪那個哭,就想著強情節(jié)。我不同,我不會不要“強情節(jié)”,但會更強調“情感”放第一位。因此拍起來會是不一樣的感覺,甚至出乎我自己的想象。就像我們在片場經(jīng)常聊,這個事情如果你我碰到了會怎么做?這個角色又會如何選擇?找出相通之處,這個情感就會很真實。就像有時候我并不要求演員哭,但他入了戲,進入了那種情感,自然地掉下了眼淚,卻會是很真實的感覺。反過來,很多地方我會選擇“留白”來處理,就像一篇篇散文,看起來很美。
記者:這種“內斂”的情感,有收有放的情節(jié),其實更耐人尋味。
劉俊杰:對,也許是過了那個年齡。過去我可能會想很多的花樣、很多的技法去呈現(xiàn),但現(xiàn)在就像金庸先生說的,重劍無鋒。拍戲時我就常常對演員說:這個鏡頭你很傷心,我不見得要你哭。你很開心,也不一定要笑。重要的不是表象,而是呈現(xiàn)出真實的情感。最難過的時候,淚光只要在眼眶里閃爍,也許比流出來更能打動人。例如姜生再見涼生,千言萬語只化成一句簡單的對白:“哥”,已足夠讓人心碎。
就像我拍一場姜生去跟小九告別的戲,姜生叫她開門。小九不理姜生,不開門。姜生就說,我要到法國去,來跟你說再見。不管你在不在門后,我都想告訴你,我好想以前的你、以前的我、以前的涼生。可是,我們都回不去了。然后姜生走了,小九其實也比誰都傷心,但還是沒有開門。這場戲看上去很簡單,但我拍了近5分鐘的長鏡頭,因為不想切來切去讓畫面碎掉。同時,我也沒有讓小九哭出來。這就是一種“安靜”的呈現(xiàn)方式,卻有特別的味道。
記者:您不想要沒有情感的強情節(jié),不想要夸張的表演,因為那樣狗血?
劉俊杰:許多電視劇追求“強情節(jié)”,一場接著一場想讓人透不過氣來,但其實并不好。就像兩個人吵架一樣,有的人希望一場接一場地展現(xiàn)極端化沖突,罵粗話打耳光等等。但對于我來說,吵架的過程反而不重要,戲劇不管怎么樣,應該是溫暖的。微妙的情感才是我想呈現(xiàn)的。
就像劇里程天佑、程天恩兩兄弟從小有很大的誤會,程天恩甚至用極端的方式對待自己的哥哥,但他還是愛自己的哥哥,最后兄弟之間一定會有化解。電視劇有社會責任,需要給人溫暖的力量。
記者:射箭要先拉后放才有力,從戲劇來說也是如此,刻意強情節(jié)反而會是弱情節(jié),所以更需要有時“散文化”地收一收。
劉俊杰:如果只有快節(jié)奏、強情節(jié),你看過就看過了,很難再回味再思考。就像彈鋼琴一樣,你只會哐哐哐,或者唱歌你只有高音,這都不太好。一個人不可能每天都處于極端狀態(tài),時刻都端著,時刻都打了雞血,時刻都歇斯底里,這都不正常不真實。真實,才是人,不完美的完美。
就像我們這次去法國看景,當?shù)氐娜藥覀內グ7茽栬F塔、香榭麗舍大街、凱旋門之類的地方,都是很漂亮很著名的景點。我說,這都不是我想拍的地方。他說這一看就是法國啊。確實一看是法國,但這是旅游節(jié)目要拍的,或者拍一個在法國的中國游客,而我拍的是角色在法國巴黎生活,他應該住在一個很有生活味道的地方。
《涼生,我們可不可以不憂傷》挑演員追求“人戲合一”,要心態(tài)不要姿態(tài)
記者:那么,您挑演員的理念又是怎樣的呢?
劉俊杰:找三個人演姜生,都表演到位,也會有三種感覺。每個人的藝術呈現(xiàn)都會不同,我會有自己獨特的理解和風格。這次找演員,一般的電視劇都是你很會表演,你能演好這個角色,所以我請你來。但這次我反過來了,因為你的內心能找到這個角色,所以我用你。這樣的話,演員就不用演了,因為你就是角色,角色就是你自己。
當然,這也意味著找演員的工作量很大,每個演員我都親自去見,都起碼談了半個小時,去找他的內心。我盡量按這個標準去找,有時一天要見二三十個演員,但大部分工作最后都完成了。所以這部戲的演員幾乎都不用演戲。我把他們放在戲里,又會有新的火花。就像程天佑請的是鐘漢良,馬天宇和孫怡則是涼生、姜生,他們三個組合在一起,又跟我當初設想的有些不一樣。
他們會有他們的想法,但沒有關系,我尊重每個人的想法。我們一起來聊,找到平衡點,然后我們把它拍出來。這是一個很有趣的,電視劇是大家共同完成的作品,不是說這是導演一個人的作品,都要聽導演的。不是這樣的,這是每一個人的作品。我只是完成一個導演在團隊中工作,提供我的想法,用我的經(jīng)驗,和大家一起把畫面呈現(xiàn)出來。
所以,我也會跟大家一起分享自己的想法,就像此刻我跟你分享自己的理念和想法一樣:我想要的是情感,而不只是情節(jié);我想要的是心態(tài),而不是姿態(tài)。這就是我在《涼生,我們可不可以不憂傷》這部電視劇里做的改變。
記者:有角色的情感和心態(tài)的話,演員更容易演繹到位?
劉俊杰:有一場戲,程天佑失明之后,跟姜生失去了聯(lián)絡,但兩個人都在巴黎。一天,兩人街頭相遇了。程天佑掉了拐杖,姜生拾起,走過去遞給他。姜生是久別重逢的感覺,但程天佑眼睛看不見、認不出。跟演員說戲時,為什么會失明?為什么是巴黎?為什么會相遇?解釋起來需要講一大堆情節(jié)和事件。所以我不這樣說,我跟演員說:下著雨的巴黎,哭著的我,失明的你。這樣他們反而一下子懂了,然后只需要找到那種情緒。
所以我跟演員講情感、講心態(tài),講情緒,而不是這個情節(jié)那個情節(jié)怎么樣怎么樣,該怎么樣演。專業(yè)演員很清楚該怎么做,用不著告訴他們,按照劇本先彎腰,再把拐杖撿起來,遞過去,再說那句臺詞。這些動作也一點都不重要了,我要的是,你呈現(xiàn)出此時此刻角色的情感。所以說拍戲,我更想拍人的情感,這樣拍起來會比較不一樣。
記者:不要“形似”,而要“神似”?
劉俊杰:這部戲的演員都是我自己挑的,基本達到了我心目中的角色特點。因為《涼生,我們可不可以不憂傷》的每個角色都可以說很難演,沒有大量的對白,又都有太多的故事了,太多的事情了。但既然難演,就干脆不要演。你得去理解這份情感,有想法才能詮釋這個角色。如果要去演,怎么演都會落了痕跡。我要你就是他,要渾然天成。因此,找到“感同心受”的那個人,放在那里就對了嘛。
這種方式很有意思,整個思考邏輯包括我自己都進行了改變。包括在現(xiàn)場,拍之前我會把演員請過來排一次。演員看到的都是戲中的對手,不是跟副導演對詞,那樣的效果會不一樣。
記者:表演很可怕的是有演員無角色、有眼淚無情感。
劉俊杰:這次《涼生,我們可不可以不憂傷》我還有一次很大的嘗試,我把對白量盡量降到最低,只說該說的話。因為很多電視劇,都靠對白去講故事,可以不看電視機,光聽就知道情節(jié)了。但電視應該要看的,我就想更多信息通過影像和演員去呈現(xiàn)。我讓演員自由發(fā)揮,走進房間,你想坐就坐。你覺得這個角色應該站到窗前,那你就站到窗前去。
通常拍戲是演員去配合我們,他在一個范圍內表演,但那樣會限制住他。我不用演員配合我,相反,我會去捕捉演員的情緒,跟著他們走。我們都服務這個作品,重要的是他進入了那個角色,然后會有無限發(fā)揮的空間。我在現(xiàn)場還經(jīng)常給大家放音樂聽。音樂帶動大家情緒進去了,入了戲,有了戲感,這就會完全不一樣。不用你說太多,他們也會知道該做什么。
這就像制片人給我的空間。我來拍這個戲的時候,她告訴我四個字:沒有預算。這很不得了,但還是要看你怎么解讀,一種是無限小,你得省著點拍,一種是可以無限大。你當然不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,敢這么說一定是互相有默契,所以這部戲我拍得很舒服。就像我說演員一樣,我不會限制你,你就去演吧,重要的是你進入那個角色。雖然有時會失焦,然后演員說對不住。我說沒關系,這個很真實,這是另外一種呈現(xiàn)方式,一般電視劇很少見。
記者:這樣其實要求更高。
劉俊杰:我自己以前也很少這樣要求演員,以前拍比較簡單。這次,就像我有一臺機器專門捕捉細節(jié),整場戲剪下來它會有很多信息量,而且當下的細節(jié)都能抓到。演員腳在動、手在干嘛,劇本上不一定有的火花都能捕捉到。不是以前那種,要拍近景就切來切去,拍完了又補個手的特寫,那都很生硬,畫面也是碎的。我也很少用腳架,我讓機器跟著角色的呼吸去律動,在軌道和搖臂上推過來搖過去,渾然天成,這很重要。
記者:沒有招數(shù),卻“無招勝有招”?所以你說審美特質像散文,像村上春樹,情感真實,神到筆在,情到景在。
劉俊杰:所以說既要真實,也要有一定的美感在里面。如果整部戲的畫面都像一幅畫一樣,那會顯得太夢幻,觀眾找不到共鳴,也容易審美疲勞。但又不能只有真實,純粹的真實是殘酷的,生活的真實也不是藝術的真實。我早期拍戲,偶像劇都用大量的柔焦,很漂亮很唯美,但我現(xiàn)在要真實,并且在真實里找到另外一種美學、另外一種美感。畫面就像油畫,我要飽和,而不是鮮艷,不一樣的感覺。
記者:所以后期的音樂、調色您都要去抓細節(jié)?
劉俊杰:每個細節(jié)只要我想到的,我都會去做。不是說把戲一拍完,后面剪輯、調光都不管了,那說明你的工作只做了三分之一。拍戲有三個階段,前期是籌備,設計,看景,談劇本和演員;中期是拍攝進行中;然后就是后制工作。很多導演只做中間這一段,把拍的片子交了走人,又進組去接另一部戲。
但我對每一部戲都希望從頭參與到尾,演員我自己想挑,景我自己要去看,每一場戲我都自己去拍、自己去剪,每個聲音、每個音樂都是我自己放進去,這樣才會是一部完整的、美學風格統(tǒng)一的作品。不然,只做了三分之一,也沒有成就感啊。
“十年涼生,此情天佑”的愛情
記者:你怎么看姜生與涼生、天佑的愛情?
劉俊杰:我在拍的時候,就覺得姜生很難,不知道該選誰。每個人看書的時候,都可以根據(jù)文字透露的情感和蛛絲馬跡,進行不同的解讀。我有幸來拍這個故事,當然會用我的方式來呈現(xiàn)。
姜生和涼生從小一起生活,開始以為是兄妹,到最后發(fā)現(xiàn)不是兄妹。別人都是想盡辦法去愛,他們卻要想盡辦法不讓自己去愛。姜生和程天佑之間,姜生跳下懸崖時,天佑眼睛都不眨跟著跳下去。
這都是很真很深很美的感情!所以說姜生真的很難選擇,無論選擇誰,都會傷到另外一個人。那我從書里找到了最好的結局:“此生相遇,便是團圓”。兩個人相愛過,此生相遇了,不管最后是否在一起,就都是最團圓的結局。
記者:也就是說對于他們三個人,沒有所謂的配角和副線?
劉俊杰:爭論誰是男一,根本沒有任何的意義。在我心里面,他們每一個都是主角。你只能說誰的戲份多一點,誰的戲份少一點,但從人物本身來說,這部戲沒有所謂的主角和配角,主線和副線。
記者:十年涼生,此情天佑,這句話其實已經(jīng)說明很多。
劉俊杰:是的,《涼生,我們可不可以不憂傷》不像一般的電視劇那種模式:一條主線、一條副線。很特別的地方在于每一條線、每一個人物都很飽滿,每一條線都可以成為一部只是篇幅有區(qū)別的電視劇。而且,我拍的時候也抱著這樣的信念:每一條線、每一個角色都要立體化、飽滿化。
也許你會覺得節(jié)奏沒有那么快,但他的情感是飽滿的,會吸引你一直想看。這也是我想要的,我不想靠那些外力,那些夸張聳動的情節(jié)來吸引人,我想用內在的情感來吸引觀眾。因為現(xiàn)在所有的情節(jié)、套路、橋段,觀眾都基本上看過了。這樣拍起來,不管拍那一場,我每天的情緒也是滿滿的,有時候收工回家還一夜難眠,因為情緒還在,還很亢奮。
《涼生,我們可不可以不憂傷》的主演和角色都是渾然天成
記者:聽說您認為程天佑非鐘漢良莫屬?
劉俊杰:“程天佑”這個角色,跟他以往的角色不太一樣。他以前的角色大多溫文儒雅,而程天佑這個角色很癡情,對姜生的愛無止盡,可是翻起臉來又很可怕,就像一面是天使,一面是魔鬼。沒有中間地帶,要么0度,要么100度。
這樣一個反差很大的角色,他以前沒有演過,對他也是一個挑戰(zhàn)。可是我想他能夠做到,程天佑非他莫屬。我就鎖定他,我說你就是程天佑。當然,還有商務、檔期之類的考量,才能達成最后的合作。拍起來之后,效果也確實很好。
記者:跟上次合作時也有區(qū)別?
劉俊杰:完全兩回事。拍《何以笙簫默》的時候,他更年輕一些,更隨性一些;而現(xiàn)在更成熟,對角色的拿捏更精準。這是一個蛻變,怎么說呢,就像一個自由自在的美國牛仔,已經(jīng)變成了一個英國紳士。對于我來說,這種轉變還很清楚,能明顯感覺到不一樣,這也很有趣很難得,我很少有機會跟一個演員合作兩次。然后這一次他一來,我第一眼就感覺整個人完全不一樣了,這兩年的歷練讓他變成熟了。這就是一個演員的成長。
記者:涼生這個角色為什么是馬天宇?
劉俊杰:交談的過程說起來很特別,我們在北京見了一次面。通常導演和演員見面,都會聊故事、聊角色,但我們沒有。我們聊孤獨、流浪,我們還聊人生、聊音樂。他也很喜歡旅行。我從他內心看到了孤獨,看到了涼生的氣質。聊完之后,我覺得這就是涼生了,不會再有另外一個人選。
記者:姜生則找了一個新人。
劉俊杰:姜生其實有不少人選,我之前沒有見過孫怡,然后從一堆照片中看到她,立刻覺得這個女孩很特別。她是一個東北女孩,個性很直,有什么話就說,有點像姜生。但姜生這個角色也很難拿捏,只是女漢子還不行,個性直還得內斂,堅強還得溫柔婉約,這些性格特質要放在一起。見面之后,她雖然很年輕,但我從她眼中還看到很多故事。不像有些戲的年輕女孩,雖然人很漂亮,但眼睛里是空的。這很難得,所以我覺得她就是姜生。
孫怡進組拍的第一場戲,是回到“魏家坪”老家。姜生小時候對父親很不原諒(恨父親背叛母親),但父母現(xiàn)在都已經(jīng)走了。那么,該如何呈現(xiàn)這種復雜的情緒呢?一般的處理都是哭天喊地,說“爸爸我回來了,過去的事都過去了”。但我們這場戲沒有一句臺詞。
她回到家,靜靜地看著父母的遺照,沒有掉一滴眼淚。然后,走進院子,把父親生前坐的有些脫落的舊輪椅,用線重新纏繞起來,再把輪椅放好,好像父親還會再坐一樣。這時,她的眼淚才掉下來。你看,這是第一場戲,一句對白都沒有,孫怡就這樣細膩地把這種復雜的情感呈現(xiàn)出來了,姜生心里的結已經(jīng)解開了。拍完之后,我覺得真找對人了,孫怡演得真好。
記者:這就是你說的“安靜的力量”,對白雖然降到最低,但信息量很大?
劉俊杰:我一直對演員說,你想哭就哭,你不想哭就不要哭。不一定要哭,才能表現(xiàn)你的傷心。就像未央婚禮那場戲,涼生在婚禮前一晚走了。在婚禮現(xiàn)場,白色的玫瑰花,白色的桌巾,只有紅色的燈籠照著,新娘穿著紅色的衣服,一個人坐在那里。我把鏡頭對著她,半身的景,然后機器開始往后拉,兩分半鐘。
我就用這樣的方式去呈現(xiàn)情感:那么大的禮堂,都是白色和紅色。陪伴新娘的卻是站著的服務員,新郎沒有來。一個鏡頭,未央所有的內心世界都展露無遺。
記者:反派角色又如何選擇的呢?
劉俊杰:反派都沒有臉譜化,壞人不一定要張牙舞爪。就像程天恩,我們看小說的時候會覺得這個人做了好多壞事。但是,我選擇了一個安安靜靜的年輕人,干干凈凈地坐在輪椅上,手上玩著魔方,靜靜地看著你,輕輕的聲音,慢慢地說話。但這樣高智商的冷靜,更讓人覺得可怕。
因此,這個演員我找了很久,也找了很多人,總感覺不對。因為這個角色是天使的面孔,做著魔鬼一樣事情。后來找到于朦朧,他很年輕,卻又很沉得住氣,安靜,不浮躁。他看著你的時候,眼神很銳利,就覺得很棒。我詮釋角色的方式有些不一樣,包括小九。我覺得拍戲最好是想象之中,意料之外。合情合理,又有新意和驚喜,我就想每個角色都是這樣的。
我挑的每一個角色,包括北小武、管家,都很不一樣。要做到這一點,就必須每個演員要自己去找去聊,而且,我不是說來看看他,坐一坐就走了。每一個演員我都至少聊半個小時,問問哪里人等,了解這個演員,因為我必須找到他的內心。
這是個很有趣的經(jīng)歷,我在找演員的過程當中,也認識了很多人,收獲了很多。就算你沒有演到這個角色,下次也可能會有合作的機會,所以說活到老學到老,雖然有時候蠻累的,一天要見二三十個演員,每個人都要聊一段時間。當然,有的其實見面三秒鐘就決定了,就像是說一見鐘情,這也是很有趣的經(jīng)歷。
《涼生,我們可不可以不憂傷》是在理想狀態(tài)下創(chuàng)作出來的結晶
記者:我感覺《涼生,我們可不可以不憂傷》的電視劇似乎比原著多了明朗、溫暖的成分?
劉俊杰:就像程天恩和程天佑,如果只是往壞里說程天恩是不對的。程天恩對程天佑的不諒解,很大程度因為他一直以為自己的腿是被哥哥害的,但其實不是。原著小說里寫的是年少時捉鴿子爬閣樓,哥哥被鴿群驚嚇不慎松手。我在劇里做了改變,變成哥哥用盡力氣也無法扶住樓梯,最后還增加了兄弟化解的戲,程天恩對程天佑說,哥,你不知道我有多愛你。
這個很重要,我不想他們兄弟之間一輩子恨來恨去。人有時會這樣,我太愛你了,卻反而在傷害你;或者,我在傷害你時,并不知道其實是因為愛你。程天恩對程天佑就是這樣的。電視劇還是要有一些社會責任,給人一些溫暖。
記者:等《涼生,我們可不可以不憂傷》殺青,你會怎么想這一部戲?
劉俊杰:其實拍完這部戲,我會不知道自己以后還會不會這樣的機會,再拍一部所有的想法都可以被執(zhí)行的戲。就像原著作者看到小說里所有的場景都被還原出來,那會是很過癮的事情。我并不想打安全牌,在套路里生存。人,尤其搞創(chuàng)作,要敢于突破,所以我也希望我拍的每部戲風格都不一樣。通常拍戲嘛,投資方會跟你聊很多,不要這個不要那個,會跟你設定一個空間。但這次制片方給了我很大的空間,包括說沒有預算。我既感到難得的支持,又覺得戰(zhàn)戰(zhàn)兢兢責任重大,還擔心以后拍戲不會這么過癮。